國際金流大剖析
熱錢橫掃全球
作者:吳韻儀
出處:天下雜誌 第381期 2007/09/26 出刊
美國次級房貸風暴,讓法國銀行爆發危機、英國銀行擠兌、全球股市重跌,複雜、連動、變幻莫測的全球金融市場,像無形的巨浪席捲世界,這股金流巨勢力從何而來?流向何處?投資人如何在驚濤駭浪中抓對方向?
初秋的華盛頓,近午的陽光從整片弧形的窗戶,灑進葛林斯潘的辦公室,明亮溫暖。
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穿著簡單的白襯衫,八十一歲了,他仍然不時敲著辦公桌彭博社特殊設計的電腦鍵盤。只要按一個鍵,他就可以看到世界任何一個市場、這一秒的變化。任何變化,葛林斯潘似乎都可以從容解讀,直指核心。
「美國次級房貸的問題,怎麼到了歐洲,我真的搞不清楚,」葛林斯潘在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一開始就切入最近的風暴。
原來八月上旬,法國BNP銀行(BNP Paribas)緊急凍結旗下三個投資美國次級房貸的基金,引爆歐洲市場危機。歐洲央行緊急輸血,一日之內挹注了九百五十億歐元的巨額資金,相當一千三百三十億美元,幾乎是台灣外匯存底的一半。
雖然暫時成功滅了火,但這自九一一以來最大的干預動作,讓市場信心潰堤,資金迅速位移,連台灣股市都深受外資收手的波及。
潮流變化:葛老坦言金融巨獸已難掌握
「全球金融巨獸已經過度發展,市場已經變得太大、太複雜、變動太快,最老練的人也無法完全掌握,」葛林斯潘坦白直接地說。大家都知道,新風險時代已經來臨,只是不知道,下一個引爆點,會落在哪裡。
全球金融巨獸的警語來自葛林斯潘,意義尤其深遠。
葛林斯潘擔任美國聯準會主席長達十八年,歷經四任總統、碰過兩次金融風暴,仍然讓美國享受長達十年的經濟榮景。
在他的指揮下,美國聯準會電子支付系統每天處理的金流數量,達四兆美元,遍及美國與世界各國銀行的交易。四兆美元的流量,相當於兩個香港股市、或六個台灣股市的市值。
批:金流量可以跟市值放在一起比較?
退休後,他在康乃狄克大道(Connecticut Avenue)上的辦公室十分低調,沒有標示、掛的門牌甚至不是他的名字,但是周圍就是美國智庫大本營,到白宮連走路也不要十分鐘,往來的仍是影響美國及世界決策的重量級人物。
記者聽完葛林斯潘解讀世界變化,朝美國國會山莊走去。就在首府路(Capital Street)上,看到美國目前呼聲最高的總統候選人希拉蕊,穿著一襲粉紫色套裝、在人群與保全簇擁下,迎面走來。美國次級房貸問題,也成了美國總統競選的棘手議題,希拉蕊主張成立十億美元基金幫助付不起房貸的窮人。
金流起源:新興國家財富力推升資金水位
為什麼全球金融市場急速膨脹,橫掃歐美及世界,成為難以掌控的巨獸?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新興國家近十年來急速的富起來了,全球資金水位大增。
二○○一年以來,全球GDP的比重,從已開發國家,向開發中國家位移。
《經濟學人》指出,過去一年來,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供給量平均成長了二一%,全球五分之三的貨幣供給成長,是來自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東南亞等新興國家。這些開發中的新興市場國家,許多都有較高的儲蓄,造成全球等待投資的資金大增。
中國大陸最近蜂擁投入股市的數字,就是最好的縮影。
今年年中,中國大陸上海加深圳股市的開戶數,突破一億大關,A股每天平均有三十萬人開戶。每個戶頭裝的都是都會白領新貴、工廠勞工、甚至鄉下農民的辛苦累積的儲蓄,急著投入股市,參與新金錢遊戲市場。
新興市場為金融市場提供源源不絕的新血,但是真正從中獲利的卻是老牌的金融中心。他們不斷發展金融技術,不斷推出衍生性金融商品,讓世界的金流,倍數擴張,運作更為複雜。
例如美國的次級房貸引爆危機,是房貸金融機構,一手把錢貸給不符貸款條件的客戶、追求業績,另一手又把信用不好的客戶所帶來的風險、包裝成新的證券化金融商品賣出,證券商品層層轉賣,最後風險難以計算,更不知落到誰家。
幕後玩家:新衍生金融商品將風險帶到全球
離開美國,到達倫敦。
老牌中的老牌,倫敦,發展金融服務超過三百年,今年重登世界金融中心寶座,靠的就是創新金融服務。
今天,全球四二%的國際股票在倫敦交易,超越紐約、成為世界第一;每天,全球三二%的外匯交易在倫敦操作,金額比紐約加東京還高。就連美國電影公司要拍知名的金錢遊戲電影《華爾街》的續集,也順應時勢,把場景移至倫敦。
倫敦的急速崛起,部份是靠新興的回教金融,倫敦是穆斯林國家以外最大的回教金融市場;高獲利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倫敦佔了歐洲對沖避險基金的七九%、世界的二一%。
現在登上千禧年所建造的摩天輪倫敦眼,不論是往北看到大英博物館,還是往南看到白金漢宮,到處都看得到高架起重手臂,高樓大廈一再翻新,建設再建設,為了吸引更多的錢、更多的人。
不論是中東油元、俄羅斯資金、印度與中國大陸的IPO、北歐的退休基金,倫敦都全力爭取到口袋,再切割、包裝成新的金融商品,推向世界,一塊錢也不能閒著不動。
「我們就是要讓資金非常有效率,」荷蘭銀行(ABN-AMRO)衍生性金融商品副總裁沃爾(Robert Waugh)說。
沃爾是位物理博士,擅長建立數學模型,一派英國紳士。他站在倫敦新交易所的玻璃帷幕中庭,談起衍生性金融商品,「我就像生魚片師傅,」他一面說、一面舉起雙手上下揮動,細黑框眼鏡後的大眼睛跟著瞇起來,像在精準打量,「魚的每一個部位都有價值。」切準對的部位、給有需要的人,就可以拿到最好的價錢。任何資金、風險,只要無法轉手,就是浪費,他說。
今天倫敦這樣的大交易所,已經完全電子化。三、 四十年前,股市只能買賣股票與債券,現在各種複雜的衍生金融產品也在其中交易,數量與複雜度都大幅提升。譬如,五十年前,紐約交易所一天成交幾百萬股,現在一天的交易量早就超過二十億股。
資訊化加上全球化,一小時接一小時,不同時區、不同地點、不同風險的產品,在現代交易所裡不斷轉手。
金流快速流動、橫掃,幾個電腦鍵盤輕敲,就能掀起滔天大浪,每個股市都逃不掉。整個世界已經被連在一起,哪個角落出了問題,其它市場也被牽著動。就像明明是美國品質不良的房貸,結果最先需要急救的竟然是法國銀行與歐洲。
風險跟著資金、被數學模式帶著全球跑,誰也算不準新的風暴會起自何方。
剛訪問完葛林斯潘,搭飛機橫越大西洋,《天下雜誌》記者卻親眼目睹英國三十年來罕見的擠兌風潮。
英國第五大的房貸銀行北岩(Northern Rock),靠創新房貸商業模式,近年在英國快速成長。
最近房貸市場資金水位一下降,它的資金就短缺,向英國財政部求助,立刻引爆信心危機。
九月十五日星期六,清晨六點開始,前一天沒有領到錢的存戶,從蘇格蘭、曼徹斯特各地,紛紛趕到北岩在倫敦市郊唯一周末營業的分行,排隊等著九點開門提領存款。不到兩個小時,就已經聚集了兩三百人,在清晨的寒風中,鼻子都吹紅了。
一天之內,存戶從北岩的網路與實體銀行提出的金額,高達十億英鎊,相當於六百六十七億台幣。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立刻宣布全力支援紓困。
全球發燒:新興市場爭相建設金融中心
「想要賺錢,就要甘冒風險,」倫敦金融市市長史圖塔(John Stuttard)在官邸面對《天下雜誌》記者及十幾位歐洲新聞同業說明北岩銀行的衝擊,更像是對大眾的信心喊話。
金融市,是倫敦的城中之城,就像皇冠上最閃亮的寶石,吸引、輸出倫敦的金融投資。世界主要銀行、各國金融監理單位,都在這裡設有辦公室。
位在金融中心的市長官邸,會議室牆上掛滿了私人收藏名畫,長長的會議桌上吊著華麗的水晶燈。
就在這同一個會議室、同一張會議桌上,來自中國、中東、紐澳等不同國家的銀行家、金融官員,川流不息,都希望向倫敦取經。
隨著金融商品一再衍生,金融中心跟著多元化、區域化、特色化,世界各國建立金融中心,正流行。杜拜、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首爾、吉隆坡等新興富裕市場,尤其積極。瑞典、丹麥、俄羅斯、盧森堡、愛爾蘭、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的記者,都異口同聲說金融是自己國家當下的發展重點。
「金融中心能夠吸引更多的資金、創造最高薪的工作,」《愛爾蘭時報》記者斯萊特(Laura Slattery)一語道破,她經常往返倫敦,就近觀察,「愛爾蘭的經濟發展到了瓶頸,發展金融中心絕對是下一步。我們應該可以找出自己的特色。」
斯萊特的回答,也說出了大家心裡同樣的想法。貪婪與恐懼,金融同時挑動人們心底兩種情緒。不論情況如何,總要找條路繼續往世界市場衝。
金錢遊戲方興未艾,一波接著一波,後浪不斷衝擊前浪。
台灣危機:不屬任何國際貨幣組織,將無法求援
當英國北岩銀行風暴還沒有完全落幕,渣打銀行又購併美國運通銀行,英國金融勢力,再下一城。去年,渣打也併購台灣的新竹商銀。
但同時期,中東的卡達和杜拜又以豐沛的新油元,爭搶著要購買倫敦證交所二○%與二八%的股權,顯示阿拉伯國家也要擠上世界金流主戰場的企圖心。
不論主動或被動,台灣與國際的連動,一定愈來愈緊密,也很難自外於國際金流狂潮橫掃的風險。今年七、 八月受外資帶動的股市震盪,記憶猶新。
世界金流橫掃下,台灣要扮演什麼角色?
但台灣只是金流中的一條小船,台灣的股市市值至今年八月為六七八二億美元,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倫敦的六分之一。
在討論台灣經濟未來的挑戰與機會的論壇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孟岱爾(Robert Mundell)提醒,台灣不屬於任何國際貨幣組織,一旦面臨金融危機,無法求助國際組織紓困,兩千六百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仍是台灣堅實的靠山。
台灣無法自外於世界,對風險與變化的應對,卻要格外的靈巧與謹慎。
風險新世界,已經到來。
專訪葛林斯潘:金融巨獸難以駕馭的挑戰
我們的新世界(平裝版)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艾倫.葛林斯潘
Part 1 - 引言
物理學在過往的歷史中,嚐試將眾多現象綜合為很少幾個理論。例如,在早期,人們觀察到運動的現象和熱的現象;還有聲、光和重力的現象。但在牛頓 (Sir Issac Newtown, 1642-1727) 解釋了運動的規律以後,人們很快發現,這些過去看起來毫不相干的現象,其實是同一事物的側面。例如,聲音現象完全可以理解為空氣中原子的運動。所以聲音不 再被看作是運動之外的什麼事了。人們還發現,從運動規律出發,熱現象也是容易理解的。用這個方式,一大堆物理學理論被綜合成一個簡明易懂的理論。不過萬有 引力理論除外,它不能用運動規律來理解,甚至在今天它也還是與其他理論毫無聯繫。迄今,萬有引力不是借助其他現象所能理解的。
在把運動、聲和熱這幾種現象綜合起來之後,人們又發現了我們稱之為電現象和磁現象的幾種現象。1873年,這些現象同光和光學現象被馬克斯威 (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 的一個理論綜合在一起,Maxwell 提出光就是電磁波。所以在這個階段,有運動定律、電和磁的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
1900 前後,一種解釋物質到底是什麼的理論出現了。它被稱為物質的電子理論~認為原子中有很小的帶電粒子。這個理論逐漸演化發展,認為原子中有一個重核,並有電子繞它旋轉。
人們想借助力學定律,就是說想仿照牛頓利用運動定律探究出地球如何繞日運行的辦法來理解電子繞核旋轉,這個努力是徹底失敗了:它做的所有預言都是錯的。(附帶說一句,相對論大致也是這段時間裡提出來的,你們大家都把它理解成是物理學中的一場革命。但與牛頓運動定律不能用於原子這個發現比起來,相對論只是個小修正。)建立另一個體系取代牛頓定律花費了很長時間,因為原子水平上的現象是很奇怪的。要領悟在原子水平上發生的事情,人們必須拋棄常識。最後, 在 1926年,用來解釋電子在物質中的「新型行為」的一種「非常識性」理論建立起來了。這個理論看來好像荒誕不經,但事實上當然絕非如此:它就叫做量子力 學。「量子」這個詞是指自然界那個違背常識的特別的一面。我準備和你們談的,就是關於這一面的問題。
量子力學的理論還解釋了所有各類現象的細節,例如為什麼一個氧原子和兩個氫原子合成水,等等。這樣,量子力學就也為化學提供了背景理論。所以說基礎的理論化學實際上就是物理學。
量子力學由於能夠解釋物質的所有化學性質和其他各種性質而獲得極大的成功。但關於光和物質的相互作用還是存在問題。就是說必須將 Maxwell 的電和磁的理論加以改造,使之與已經建立起來的新的量子力學相適應。這樣,在1929年,一種新的理論~關於光和物質相互作用的量子理論~終於由一些物理學家建立起來了。它的名字倒是怪可怕的,叫做量子電動力學。
但是這個理論曾有過讓人頭疼的麻煩。如果你粗略地進行計算,這理論能給你相當合乎邏輯的結果。但要是想進行更精確的計算,修正值會越來越小吧?例如一系列的修正值中,(下一個會比上一個小)~但實際上很大~事實上竟然是無窮大!原來,這個理論不允許你把任何一個量計算得超過一定的精度。
Part 2 - 光子:光的粒子
這是關於量子電動力學系列講座的第二講。顯然諸位上次都不在座(因為上次我告訴大家,他們別打算聽懂任何東西),所以我先把第一講的內容簡要地總結一下。(猜:第二講的聽眾人數比第一講多,費曼開玩笑說:啥?上次講的東西,居然沒把人嚇光?)
第一講我們講的是光。光的第一個重要特點,它看起來是粒子:如果我們用非常微弱的單色光(只有一種顏色的光)打到探測器上,那麼當光越來越弱時,探測器作響的次數就越來越少,但每次作響的聲響大小不變。(想:如果光只是波動,弱光只是振幅的減弱,探測器應該聽到變弱且持續的聲響,而不是一樣大聲但間歇次數降低的聲響。)
上一講討論光的另一個重要特性是:單色光的部份反射。打到玻璃單一表面的光子有 4% 被反射回來。這點已經是個艱深的奧秘了,因為不可能預測哪個光子反射回來,哪個光子穿透過去。在加上第二個表面後,結果更是奇怪,兩個表面的部份反射並非期望的 8%,而是可以高達 16%,或者完全沒有(反射)~究竟結果如何,則取決於玻璃的厚度(註:兩個表面之間的距離)
兩表面部份反射的奇怪現象,在強光的情況,可以利用波動理論來解釋;但波動理論不能解釋~在光越來越微弱的狀況,探測器發出的~搭、搭、、聲總是一樣的響。量子電動力學"解決"了這個「波粒二象性」的問題,它的說法是,光是由粒子組成的(正如牛頓原來的設想一樣),但巨大的科學進步的代價~物理學被迫向後撤退,撤退到它只能計算的只是一個光子打中探測器的機率~這個地步,而無法給出一個很好的模型來說明:實際發生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比較仔細地研究一下這一小束光:把光源放在 S,光電倍增管在 P,S 與 P 之間安放一對屏障,以防光路太散(圖 33)。我們把第二個光電倍增管放在 P 下方的 Q,為了簡單起見,再次假設:光只沿著成一角度的兩段直線所構成的路徑從 S 到達 Q。好!我們看會怎樣呢?在兩屏障之間的距離大得足以容納多條彼此靠近的到達 P 路徑和到達 Q 的路徑時,到達 P 的路徑箭頭相加是彼此增長的(因為所有到 P 路徑都需要幾乎相同的時間),而到達 Q 路徑的箭頭卻都彼此相消(因為這些路徑所需的時間大不相同)。所以,Q 點的光電倍增管就不會作響。
但是,讓我們把兩個屏障推得彼此靠近,當接近到某一個程度時,Q 的探測器開始作響!在兩屏障間的空隙小到幾乎合攏,因而只有很少幾條緊鄰的路徑可以通過時,到 Q 的那些箭頭也彼此相長了,因為它們所需時間也幾乎沒有差別(圖 34)。當然,P、Q兩處的最終箭頭都是很小的,所以無論到 P 還是到 Q 都沒有多少光能通過這個小孔,而 Q 探測器作響的次數幾乎和 P 一樣多!所以,當試圖把光路壓得極窄以確定光只走一條直線時,光會因為壓得太窄而拒絕合作,並開始散射開來。

[3] 這是「測不準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 的一個例子:關於光在兩屏障間走哪條路?和此後走哪條路?這兩個知識之間有一種"互補"關係 ~ 想要精確地知道是不可能的!我願意把測不準原理放在它的歷史地位上來考察:在量子物理的革命性思想剛剛提出的時候,人們還力求借用老觀念(如:光走直線)去理解一些現象。但到了一定的時候,老觀念開始不靈光了,於是出現了這樣的警告:事實上,"當___時,你的老觀念就一文不值了。" 如果放棄所有的老觀念,換成這個講座提到的~將單一事件的所有可能方式的箭頭都加起來 ~ 測不準原理就不再需要了。


 「七欠有一種功夫,當年老師傅在唐山打死人,~功夫練到最好,練到會輕功,會飛的意思~就對了!」(@@~~~ 眨眼~~)
「七欠有一種功夫,當年老師傅在唐山打死人,~功夫練到最好,練到會輕功,會飛的意思~就對了!」(@@~~~ 眨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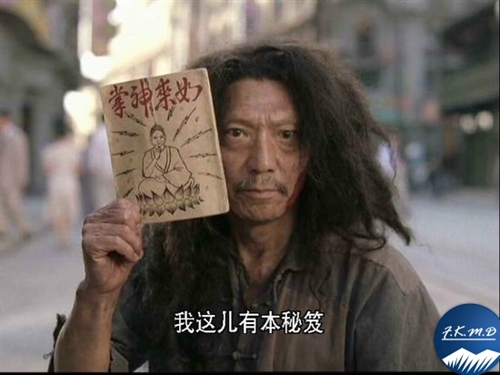 「可是最後失傳了~沒有人會這一套~」(囧!洩氣~~~)
「可是最後失傳了~沒有人會這一套~」(囧!洩氣~~~)
 當年,愛迪生透過媒體、輿論醜化特斯拉的交流傳輸裝置。或許正因如此,特斯拉也聲名大噪。~特斯拉一向孤僻,突然吸引到眾多目光,在特斯拉身上產生了奇怪的影響。這段期間,他最愛做的事情就是在實驗室中工作一整天後,換上晚禮服,招輛計程車到豪華飯店中參加晚宴,或到紐約的時髦餐廳參加有錢朋友的聚會。吃過飯後,他會邀請同伴參觀實驗室,展示自己的發明,用許多把戲和驚人的視覺效果,為來賓製造一場震撼教育。~他所描述的古怪實驗,以及電的種種神祕力量,總是能在煩悶無聊的餐會上令社交名流興奮不已。
近年,藉由電影的推波助瀾,特斯拉更加增添神秘色彩。有一些人相信:
當年,愛迪生透過媒體、輿論醜化特斯拉的交流傳輸裝置。或許正因如此,特斯拉也聲名大噪。~特斯拉一向孤僻,突然吸引到眾多目光,在特斯拉身上產生了奇怪的影響。這段期間,他最愛做的事情就是在實驗室中工作一整天後,換上晚禮服,招輛計程車到豪華飯店中參加晚宴,或到紐約的時髦餐廳參加有錢朋友的聚會。吃過飯後,他會邀請同伴參觀實驗室,展示自己的發明,用許多把戲和驚人的視覺效果,為來賓製造一場震撼教育。~他所描述的古怪實驗,以及電的種種神祕力量,總是能在煩悶無聊的餐會上令社交名流興奮不已。
近年,藉由電影的推波助瀾,特斯拉更加增添神秘色彩。有一些人相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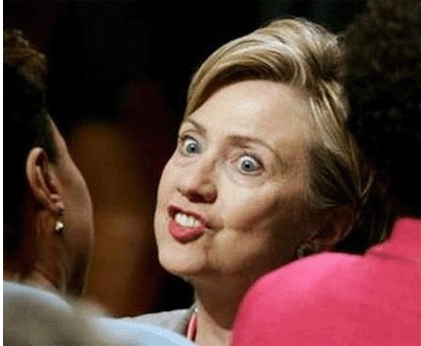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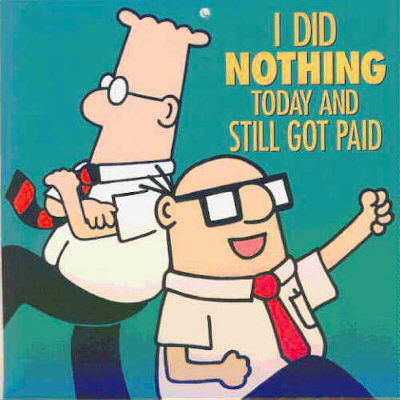 使用地表最快的處理器,經過大量的
使用地表最快的處理器,經過大量的 
